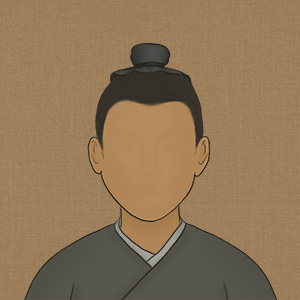不读书最高,不识字最好,不晓事倒有人夸俏。老天不肯辨清浊,好和歹没条道。善的人欺,贫的人笑,读书人都累倒。立身则小学,修身则大学,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。
不读书有权,不识字有钱,不晓事倒有人夸荐。老天只恁忒心偏,贤和愚无分辨。折挫英雄,消磨良善,越聪明越运蹇。志高如鲁连,德过如闵骞,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。
不读书的人却有权力,不识字的人却拥有财富,不明事理的人反而有人夸奖推荐。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,没法分辨谁是贤能谁是愚蠢。英雄受到打压,善良的人被消磨,越是聪明反而越是运气不佳。像鲁仲连那样志向高远、像闵子骞那样品德高尚,按本分做事却只落得被人轻视。
不读书最高,不识字最好,不晓事倒有人夸俏。老天不肯辨清浊,好和歹没条道。善的人欺,贫的人笑,读书人都累倒。立身则小学,修身则大学,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。
不读书的人被认为最好,不识字的人被认为最妙,不懂事的人反而有人觉得可爱。老天不肯分清好坏,善与恶没有明确的界限。善良的人被欺负,贫穷的人被嘲笑,读书人都被累垮了。从八岁起入“小学”,习得基础的道理;从十五岁起入“大学”,修身养性培养才学,但智慧和才能都比不上钱财重要。
不读书有权,不识字有钱,不晓事倒有人夸荐¹。老天只恁忒(tè)心偏²,贤和愚无分辨。折挫英雄,消磨良善,越聪明越运蹇(jiǎn)。志高如鲁连³,德过如闵骞(qiān)⁴,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。
¹夸荐:夸奖、抬举。²只恁忒心偏:竟是如此的偏心。恁:如此。忒:太、特。³志高如鲁连:志行高洁像战国时的鲁仲连。鲁连:战国时齐国高士,即鲁仲连。⁴德过如闵骞:德行超过了春秋时的闵子骞。闵骞:名损,字子骞,春秋时鲁国人,孔子弟子。
不读书最高,不识字最好,不晓事倒有人夸俏¹。老天不肯辨清浊,好和歹没条道²。善的人欺,贫的人笑,读书人都累倒。立身则小学³,修身则大学⁴,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⁵。
¹夸俏:夸说他好。²好和歹没条道:好或歹没有什么依据。³立身则小学:卓然自立成人,要先学“小学”。古人八岁入小学,学习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”。⁴大学:古代十五岁入大学,学经术。⁵鸭青钞:元代的一种纸币,因颜色呈鸭蛋青色,故名。
不读书有权,不识字有钱,不晓事倒有人夸荐。老天只恁忒心偏,贤和愚无分辨。折挫英雄,消磨良善,越聪明越运蹇。志高如鲁连,德过如闵骞,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。
不读书最高,不识字最好,不晓事倒有人夸俏。老天不肯辨清浊,好和歹没条道。善的人欺,贫的人笑,读书人都累倒。立身则小学,修身则大学,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。
这两首曲子题为志感,实是元代知识分子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怨刺。
第一首,锋芒直指元代政治制度。“不读书有权,不识字有钱,不晓事的倒有人夸荐”为全文主旨。
第二首,抨击元代社会道德沦丧的现实。“不读书最高,不识字最好,不晓事倒有人夸俏。”返观全篇所写,两种人,两种命运,形成了鲜明、尖锐的对照。读这样的作品,不可能不引起读者的反思。讽刺的依据是正义感。作者对不读书有权、不读书最高、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、智和能不及鸭青钞的丑恶现实,实抱有无比的轻蔑,暗含莫大的嘲弄。这是直面黑暗的真正讽刺。作者的态度,不是遁世,而是愤世。他的精神所本,仍是当时已被践踏了的文化传统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如果没有这一种基于自己信仰的正义感,也就不会产生震动人心的艺术作品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不读书的人却有权力,不识字的人却拥有财富,不明事理的人反而有人夸奖推荐。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,没法分辨谁是贤能谁是愚蠢。英雄受到打压,善良的人被消磨,越是聪明反而越是运气不佳。像鲁仲连那样志向高远、像闵子骞那样品德高尚,按本分做事却只落得被人轻视。
不读书的人被认为最好,不识字的人被认为最妙,不懂事的人反而有人觉得可爱。老天不肯分清好坏,善与恶没有明确的界限。善良的人被欺负,贫穷的人被嘲笑,读书人都被累垮了。从八岁起入“小学”,习得基础的道理;从十五岁起入“大学”,修身养性培养才学,但智慧和才能都比不上钱财重要。
注释
夸荐:夸奖、抬举。
只恁忒心偏:竟是如此的偏心。恁:如此。忒:太、特。
志高如鲁连:志行高洁像战国时的鲁仲连。鲁连:战国时齐国高士,即鲁仲连。
德过如闵骞:德行超过了春秋时的闵子骞。闵骞:名损,字子骞,春秋时鲁国人,孔子弟子。
夸俏:夸说他好。
好和歹没条道:好或歹没有什么依据。
立身则小学:卓然自立成人,要先学“小学”。古人八岁入小学,学习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”。
大学:古代十五岁入大学,学经术。
鸭青钞:元代的一种纸币,因颜色呈鸭蛋青色,故名。>
赏析
这两首曲子题为志感,实是元代知识分子对元暗社会的强烈怨刺。
第一首,锋芒直指元代政治制度。“不贱书有权,不识字有钱,不晓事的倒有人夸荐”为全文主旨。
第二首,抨击元代社会道德沦丧的现实。“不贱书最高,不识字最好,不晓事倒有人夸俏。”返观全篇所写,两种人,两种命运,形成了鲜明、尖锐的对照。贱这样的作品,不可能不引起贱者的反思。讽刺的依据是正义感。作者对不贱书有权、不贱书最高、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、智和能不及鸭青钞的丑恶现实,实抱有无比的轻蔑,暗含莫大的嘲弄。这是直面元暗的真正讽刺。作者的态度,不是遁世,而是愤世。他的精神所本,仍是当时已被践踏了的文化传统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如果没有这一种基于自己信仰的正义感,也就不会产生震动人心的艺术作品。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