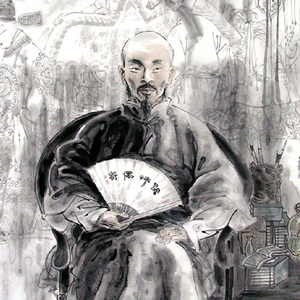吾观人之一身,眼耳鼻舌,手足躯骸,件件都不可少。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,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,独是口腹二物。口腹具而生计繁矣,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,诈伪奸险之事出,而五刑不得不设。君不能施其爱育,亲不能遂其恩私,造物好生,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,皆当日赋形不善,多此二物之累也。草木无口腹,未尝不生;山石土壤无饮食,未闻不长养。何事独异其形,而赋以口腹?即生口腹,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,蜩螗之吸露,尽可滋生气力,而为潜跃飞鸣。若是,则可与世无求,而生人之患熄矣。乃既生以口腹,又复多其嗜欲,使如溪壑之不可厌;多其嗜欲,又复洞其底里,使如江海之不可填。以致人之一生,竭五官百骸之力,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!吾反复推详,不能不于造物是咎。亦知造物于此,未尝不自悔其非,但以制定难移,只得终遂其过。甚矣,作法慎初,不可草草定制。吾辑是编而谬及饮馔,亦是可已不已之事。其止崇啬,不导奢靡者,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,亦当虑始计终,而为庶物弭患。如逞一己之聪明,导千万人之嗜欲,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,吾虑风气所开,日甚一日,焉知不有易牙复出,烹子求荣,杀婴儿以媚权奸,如亡隋故事者哉!一误岂堪再误,吾不敢不以赋形造物视作覆车。
声音之道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,为其渐近自然。吾谓饮食之道,脍不如肉,肉不如蔬,亦以其渐近自然也。草衣木食,上古之风,人能疏远肥腻,食蔬蕨而甘之,腹中菜园,不使羊来踏破,是犹作羲皇之民,鼓唐虞之腹,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。所怪于世者,弃美名不居,而故异端其说,谓佛法如是,是则谬矣。吾辑《饮馔》一卷,后肉食而首蔬菜,一以崇俭,一以复古;至重宰割而惜生命,又其念兹在兹,而不忍或忘者矣。
论蔬食之美者,曰清,曰洁,曰芳馥,曰松脆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,能居肉食之上者,只在一字之鲜。《记》曰:“甘受和,白受采。”鲜即甘之所从出也。此种供奉,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,得以有之,城市之人向卖菜佣求活者,不得与焉。然他种蔬食,不论城市山林,凡宅旁有圃者,旋摘旋烹,亦能时有其乐。至于笋之一物,则断断宜在山林,城市所产者,任尔芳鲜,终是笋之剩义。此蔬食中第一品也,肥羊嫩豕,何足比肩。但将笋肉齐烹,合盛一簋,人止食笋而遗肉,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。购于市者且然,况山中之旋掘者乎?食笋之法多端,不能悉纪,请以两言概之,曰:“素宜白水,荤用肥猪。”茹斋者食笋,若以他物伴之,香油和之,则陈味夺鲜,而笋之真趣没矣。白煮俟熟,略加酱油,从来至美之物,皆利于孤行,此类是也。以之伴荤,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,独宜于豕,又独宜于肥。肥非欲其腻也,肉之肥者能甘,甘味入笋,则不见其甘,但觉其鲜之至也。烹之既熟,肥肉尽当去之,即汁亦不宜多存,存其八而益以清汤。调和之物,惟醋与酒。此制荤笋之大凡也。笋之为物,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,凡食物中无论荤素,皆当用作调和。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,同是必需之物,有此则诸味皆鲜,但不当用其渣滓,而用其精液。庖人之善治具者,凡有焯笋之汤,悉留不去,每作一馔,必以和之,食者但知他物之鲜,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。《本草》中所载诸食物,益人者不尽可口,可口者未必益人,求能两擅其长者,莫过于此。东坡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不知能医俗者,亦能医瘦,但有已成竹未成竹之分耳。
吾观人之一身,眼耳鼻舌,手足躯骸,件件都不可少。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,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,独是口腹二物。口腹具而生计繁矣,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,诈伪奸险之事出,而五刑不得不设。君不能施其爱育,亲不能遂其恩私,造物好生,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,皆当日赋形不善,多此二物之累也。草木无口腹,未尝不生;山石土壤无饮食,未闻不长养。何事独异其形,而赋以口腹?即生口腹,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,蜩螗之吸露,尽可滋生气力,而为潜跃飞鸣。若是,则可与世无求,而生人之患熄矣。乃既生以口腹,又复多其嗜欲,使如溪壑之不可厌;多其嗜欲,又复洞其底里,使如江海之不可填。以致人之一生,竭五官百骸之力,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!吾反复推详,不能不于造物是咎。亦知造物于此,未尝不自悔其非,但以制定难移,只得终遂其过。甚矣,作法慎初,不可草草定制。吾辑是编而谬及饮馔,亦是可已不已之事。其止崇啬,不导奢靡者,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,亦当虑始计终,而为庶物弭患。如逞一己之聪明,导千万人之嗜欲,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,吾虑风气所开,日甚一日,焉知不有易牙复出,烹子求荣,杀婴儿以媚权奸,如亡隋故事者哉!一误岂堪再误,吾不敢不以赋形造物视作覆车。
我观察人的身体,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,手、脚、躯干、四肢,每一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。然而,在这些之中,唯独口腹(即饮食的需求)是原本可以不具备,但偏偏赋予了我们,从而成为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一大负担。口腹之欲一旦产生,生计之事就纷繁复杂了;生计复杂,欺诈、伪善、奸险之事也就随之而出了。这些恶行一出,就不得不设立刑罚来惩治。君主不能充分施展他的仁爱,父母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他们的慈爱,造物主虽然本性好生,但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,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最初赋予形体时的不完善,多出了口腹这一负担。你看那草木没有口腹之欲,却依然能够生长;山石土壤无需饮食,也未见它们不滋养万物。为什么唯独人类要与众不同,被赋予口腹之欲呢?即便赋予了口腹,也应该是像鱼虾饮水、蝉吸露水那样,简单滋养生命,使它们能够潜游、跳跃、飞翔、鸣叫。这样,人类就可以与世无求,避免许多因口腹之欲而生的祸患了。但现实是,人不仅有了口腹,还滋生了无尽的嗜欲,就像溪壑永远填不满一样;这嗜欲又深不可测,如同江海般无法填满。结果,人的一生都在竭尽全力,用五官和身体的每一部分去满足这无休止的消耗,却仍然觉得不够。我反复思考,不得不责怪这造物的安排。我也知道,造物主对此或许也感到后悔,但因为规则一旦制定就难以改变,所以只能任由这过错继续下去。由此可见,制定规则时务必谨慎,不可草率行事。我编纂这本书,虽然涉及到了饮食,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目的是为造物主掩饰过失。同时,我也应该考虑周全,从始至终都保持谨慎,为世间万物消除潜在的祸患。如果我仅凭一己之聪明,去引导千万人的嗜欲,那么不仅会导致禽兽昆虫等生物无法生存,我还担心这种风气会愈演愈烈。谁能知道,未来会不会再次出现像易牙那样烹子求荣的人,或者为了取悦权贵而杀害婴儿,重演隋朝灭亡的悲剧呢?一次错误已经足够可怕,岂能再犯第二次?因此,我不敢不将赋予人类形体和口腹之欲视为前车之鉴,时刻警惕。
声音之道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,为其渐近自然。吾谓饮食之道,脍不如肉,肉不如蔬,亦以其渐近自然也。草衣木食,上古之风,人能疏远肥腻,食蔬蕨而甘之,腹中菜园,不使羊来踏破,是犹作羲皇之民,鼓唐虞之腹,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。所怪于世者,弃美名不居,而故异端其说,谓佛法如是,是则谬矣。吾辑《饮馔》一卷,后肉食而首蔬菜,一以崇俭,一以复古;至重宰割而惜生命,又其念兹在兹,而不忍或忘者矣。
关于声音之道,弦乐(丝)不如管乐(竹),而管乐又不如人声,这是因为它们逐渐接近自然之音。同样地,我认为在饮食之道上,细切的肉(脍)不如整块的肉,而整块的肉又不如蔬菜,这也是因为它们逐渐接近自然之味。穿着草衣,以树木果实为食,这是上古时代的风尚。人们如果能远离肥腻之物,甘于食用蔬菜、蕨类,让腹中的“菜园”不被“羊”(象征贪欲)所践踏,那就如同生活在伏羲、黄帝的时代,拥有唐尧、虞舜般的质朴生活,这与崇尚古玩、追求古朴雅致的情趣是相一致的。我所感到奇怪的是,世间有些人却舍弃了这些美好的名声不去追求,反而故意标新立异,声称这是佛法的教导。这实在是谬误啊。我编纂《饮馔》这一卷,将蔬菜置于肉类之前,一是为了崇尚节俭,二是为了复古;同时,我也非常重视减少宰杀,珍惜生命,这是我一直念念不忘、不忍忽视的事情。
论蔬食之美者,曰清,曰洁,曰芳馥,曰松脆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,能居肉食之上者,只在一字之鲜。《记》曰:“甘受和,白受采。”鲜即甘之所从出也。此种供奉,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,得以有之,城市之人向卖菜佣求活者,不得与焉。然他种蔬食,不论城市山林,凡宅旁有圃者,旋摘旋烹,亦能时有其乐。至于笋之一物,则断断宜在山林,城市所产者,任尔芳鲜,终是笋之剩义。此蔬食中第一品也,肥羊嫩豕,何足比肩。但将笋肉齐烹,合盛一簋,人止食笋而遗肉,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。购于市者且然,况山中之旋掘者乎?食笋之法多端,不能悉纪,请以两言概之,曰:“素宜白水,荤用肥猪。”茹斋者食笋,若以他物伴之,香油和之,则陈味夺鲜,而笋之真趣没矣。白煮俟熟,略加酱油,从来至美之物,皆利于孤行,此类是也。以之伴荤,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,独宜于豕,又独宜于肥。肥非欲其腻也,肉之肥者能甘,甘味入笋,则不见其甘,但觉其鲜之至也。烹之既熟,肥肉尽当去之,即汁亦不宜多存,存其八而益以清汤。调和之物,惟醋与酒。此制荤笋之大凡也。笋之为物,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,凡食物中无论荤素,皆当用作调和。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,同是必需之物,有此则诸味皆鲜,但不当用其渣滓,而用其精液。庖人之善治具者,凡有焯笋之汤,悉留不去,每作一馔,必以和之,食者但知他物之鲜,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。《本草》中所载诸食物,益人者不尽可口,可口者未必益人,求能两擅其长者,莫过于此。东坡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不知能医俗者,亦能医瘦,但有已成竹未成竹之分耳。
谈论蔬菜美食的美妙之处,主要在于它的清新、洁净、芬芳和松脆。然而,真正让它超越肉食之美的,只在于一个“鲜”字。《礼记》有云:“甘味受和于五味之中,白色受采于五色之内。”这里的“鲜”,正是甘甜之味的源泉。这种鲜美,只有那些亲自在山林间耕作的山僧野老才能享受到,而城市中依赖卖菜为生的人,则难以体会。不过,对于其他种类的蔬菜,不论是城市还是山林,只要宅旁有菜园,随时采摘烹煮,也能时常感受到其中的乐趣。至于竹笋,则绝对是山林中的瑰宝。城市中虽也有售卖,但无论其如何芳香鲜美,终究只是竹笋之味的残余。竹笋是蔬菜中的第一品,肥羊嫩猪,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如果将竹笋与肉同煮,人们往往只吃竹笋而留下肉,由此可知,竹笋之美,犹如熊掌之珍贵,而肉则如同鱼般普通。购买于市场的竹笋尚且如此美味,更何况是刚从山中挖出的新鲜竹笋呢?竹笋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,难以一一详述,但简而言之,就是“素煮宜用清水,荤煮宜配肥猪”。素食者食用竹笋时,若以其他调料或油脂相伴,反而会掩盖其本真的鲜美,失去竹笋的真谛。最佳的方式是白水煮熟,略加酱油调味。自古以来,至美之物往往都是单独食用最能体现其风味,竹笋亦是如此。若以竹笋搭配荤食,则牛羊鸡鸭等皆非最佳选择,唯有猪肉最为相宜,且以肥猪肉为佳。但这里的“肥”并非追求油腻,而是因为肥猪肉能带来甘味,这种甘味与竹笋的鲜美相结合,非但不会显得油腻,反而会使竹笋的鲜美更加突出。烹饪时,待肉熟后应将肥肉去除,汤汁也不宜多留,只需保留其精华,再加入清汤调和。调味时,只需醋与酒即可。这便是烹饪荤笋的大致方法。竹笋不仅单独食用或搭配其他食材都能展现其美味,更妙的是它还能作为调和之物,提升各种食材的风味。正如菜肴中的竹笋与药物中的甘草一样,都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。有了竹笋的加入,各种食材都能变得更加鲜美。但使用时应注意,不要使用竹笋的渣滓,而要充分利用其精华。善于烹饪的厨师,都会将焯竹笋的汤水留下,每次做菜时都加入一些,使得菜肴更加鲜美,而食客往往只知食物本身之鲜,却不知这鲜美之源乃是竹笋之汤。《本草》中所记载的许多食物,有的虽然对人体有益却不一定可口,有的虽然可口却不一定有益健康。而竹笋则能两者兼顾,既美味又健康。苏东坡曾说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其实,竹笋不仅能治愈人的俗气,还能让人保持健康,避免瘦弱。只不过,这里的“竹”有已成之竹与未成之笋之分罢了。
吾观人之一身,眼耳鼻舌,手足躯骸(hái)¹,件件都不可少。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,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,独是口腹²二物。口腹具而生计繁矣,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,诈伪奸险之事出,而五刑不得不设。君不能施其爱育³,亲不能遂其恩私,造物好生,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,皆当日赋形不善,多此二物之累也。草木无口腹,未尝不生;山石土壤无饮食,未闻不长养。何事独异其形,而赋以口腹?即生口腹,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,蜩(diāo)螗⁴之吸露,尽可滋生气力,而为潜跃飞鸣。若是,则可与世无求,而生人之患熄矣。乃既生以口腹,又复多其嗜欲,使如溪壑⁵之不可厌;多其嗜欲,又复洞其底里,使如江海之不可填。以致人之一生,竭五官百骸之力,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!吾反复推详,不能不于造物是咎。亦知造物于此,未尝不自悔其非,但以制定难移,只得终遂其过。甚矣,作法慎初,不可草草定制。吾辑是编而谬(miù)及饮馔(zhuàn),亦是可已不已之事。其止崇啬,不导奢靡者,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,亦当虑始计终,而为庶物弭患。如逞一己之聪明,导千万人之嗜(shì)欲,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,吾虑风气所开,日甚一日,焉知不有易牙复出,烹子求荣,杀婴儿以媚权奸,如亡隋故事者哉!一误岂堪再误,吾不敢不以赋形造物视作覆车。
¹躯骸:躯壳;身体。²口腹:口和腹,多指饮食。吃喝。 ³爱育:爱护养育。⁴蜩螗:蝉的别名。⁵溪壑:溪谷。
声音之道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,为其渐近自然。吾谓饮食之道,脍不如肉,肉不如蔬,亦以其渐近自然也。草衣木食,上古之风,人能疏远肥腻,食蔬蕨而甘之,腹中菜园,不使羊来踏破,是犹作羲皇之民,鼓唐虞之腹,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。所怪于世者,弃美名不居,而故异端其说,谓佛法如是,是则谬矣。吾辑《饮馔》一卷,后肉食而首蔬菜,一以崇俭,一以复古;至重宰割而惜生命,又其念兹在兹,而不忍或忘者矣。
论蔬食之美者,曰清,曰洁,曰芳馥(fù)¹,曰松脆²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,能居肉食之上者,只在一字之鲜。《记》曰:“甘受和,白受采。”鲜即甘之所从出也。此种供奉,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,得以有之,城市之人向卖菜佣求活者,不得与焉。然他种蔬食,不论城市山林,凡宅旁有圃者,旋摘旋烹,亦能时有其乐。至于笋之一物,则断断宜在山林,城市所产者,任尔芳鲜,终是笋之剩义。此蔬食中第一品也,肥羊嫩豕(tún)³,何足比肩。但将笋肉齐烹,合盛一簋,人止食笋而遗肉,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。购于市者且然,况山中之旋掘者乎?食笋之法多端,不能悉纪,请以两言概之,曰:“素宜白水,荤用肥猪。”茹斋者食笋,若以他物伴之,香油和之,则陈味夺鲜,而笋之真趣没矣。白煮俟熟,略加酱油,从来至美之物,皆利于孤行,此类是也。以之伴荤,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,独宜于豕,又独宜于肥。肥非欲其腻也,肉之肥者能甘,甘味入笋,则不见其甘,但觉其鲜之至也。烹(pēng)之既熟,肥肉尽当去之,即汁亦不宜多存,存其八而益以清汤。调和之物,惟醋与酒。此制荤笋之大凡也。笋之为物,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,凡食物中无论荤素,皆当用作调和。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,同是必需之物,有此则诸味皆鲜,但不当用其渣滓,而用其精液。庖(páo)人⁴之善治具者,凡有焯笋之汤,悉留不去,每作一馔,必以和之,食者但知他物之鲜,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。《本草》中所载诸食物,益人者不尽可口,可口者未必益人,求能两擅其长者,莫过于此。东坡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不知能医俗者,亦能医瘦,但有已成竹未成竹之分耳。
¹芳馥:芳香。²松脆:谓食物酥脆味美。³豕:猪。⁴庖人:厨师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我观察人的身体,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,手、脚、躯干、四肢,每一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。然而,在这些之中,唯独口腹(即饮食的需求)是原本可以不具备,但偏偏赋予了我们,从而成为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一大负担。口腹之欲一旦产生,生计之事就纷繁复杂了;生计复杂,欺诈、伪善、奸险之事也就随之而出了。这些恶行一出,就不得不设立刑罚来惩治。君主不能充分施展他的仁爱,父母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他们的慈爱,造物主虽然本性好生,但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,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最初赋予形体时的不完善,多出了口腹这一负担。你看那草木没有口腹之欲,却依然能够生长;山石土壤无需饮食,也未见它们不滋养万物。为什么唯独人类要与众不同,被赋予口腹之欲呢?即便赋予了口腹,也应该是像鱼虾饮水、蝉吸露水那样,简单滋养生命,使它们能够潜游、跳跃、飞翔、鸣叫。这样,人类就可以与世无求,避免许多因口腹之欲而生的祸患了。但现实是,人不仅有了口腹,还滋生了无尽的嗜欲,就像溪壑永远填不满一样;这嗜欲又深不可测,如同江海般无法填满。结果,人的一生都在竭尽全力,用五官和身体的每一部分去满足这无休止的消耗,却仍然觉得不够。我反复思考,不得不责怪这造物的安排。我也知道,造物主对此或许也感到后悔,但因为规则一旦制定就难以改变,所以只能任由这过错继续下去。由此可见,制定规则时务必谨慎,不可草率行事。我编纂这本书,虽然涉及到了饮食,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目的是为造物主掩饰过失。同时,我也应该考虑周全,从始至终都保持谨慎,为世间万物消除潜在的祸患。如果我仅凭一己之聪明,去引导千万人的嗜欲,那么不仅会导致禽兽昆虫等生物无法生存,我还担心这种风气会愈演愈烈。谁能知道,未来会不会再次出现像易牙那样烹子求荣的人,或者为了取悦权贵而杀害婴儿,重演隋朝灭亡的悲剧呢?一次错误已经足够可怕,岂能再犯第二次?因此,我不敢不将赋予人类形体和口腹之欲视为前车之鉴,时刻警惕。
关于声音之道,弦乐(丝)不如管乐(竹),而管乐又不如人声,这是因为它们逐渐接近自然之音。同样地,我认为在饮食之道上,细切的肉(脍)不如整块的肉,而整块的肉又不如蔬菜,这也是因为它们逐渐接近自然之味。穿着草衣,以树木果实为食,这是上古时代的风尚。人们如果能远离肥腻之物,甘于食用蔬菜、蕨类,让腹中的“菜园”不被“羊”(象征贪欲)所践踏,那就如同生活在伏羲、黄帝的时代,拥有唐尧、虞舜般的质朴生活,这与崇尚古玩、追求古朴雅致的情趣是相一致的。我所感到奇怪的是,世间有些人却舍弃了这些美好的名声不去追求,反而故意标新立异,声称这是佛法的教导。这实在是谬误啊。我编纂《饮馔》这一卷,将蔬菜置于肉类之前,一是为了崇尚节俭,二是为了复古;同时,我也非常重视减少宰杀,珍惜生命,这是我一直念念不忘、不忍忽视的事情。
谈论蔬菜美食的美妙之处,主要在于它的清新、洁净、芬芳和松脆。然而,真正让它超越肉食之美的,只在于一个“鲜”字。《礼记》有云:“甘味受和于五味之中,白色受采于五色之内。”这里的“鲜”,正是甘甜之味的源泉。这种鲜美,只有那些亲自在山林间耕作的山僧野老才能享受到,而城市中依赖卖菜为生的人,则难以体会。不过,对于其他种类的蔬菜,不论是城市还是山林,只要宅旁有菜园,随时采摘烹煮,也能时常感受到其中的乐趣。至于竹笋,则绝对是山林中的瑰宝。城市中虽也有售卖,但无论其如何芳香鲜美,终究只是竹笋之味的残余。竹笋是蔬菜中的第一品,肥羊嫩猪,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如果将竹笋与肉同煮,人们往往只吃竹笋而留下肉,由此可知,竹笋之美,犹如熊掌之珍贵,而肉则如同鱼般普通。购买于市场的竹笋尚且如此美味,更何况是刚从山中挖出的新鲜竹笋呢?竹笋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,难以一一详述,但简而言之,就是“素煮宜用清水,荤煮宜配肥猪”。素食者食用竹笋时,若以其他调料或油脂相伴,反而会掩盖其本真的鲜美,失去竹笋的真谛。最佳的方式是白水煮熟,略加酱油调味。自古以来,至美之物往往都是单独食用最能体现其风味,竹笋亦是如此。若以竹笋搭配荤食,则牛羊鸡鸭等皆非最佳选择,唯有猪肉最为相宜,且以肥猪肉为佳。但这里的“肥”并非追求油腻,而是因为肥猪肉能带来甘味,这种甘味与竹笋的鲜美相结合,非但不会显得油腻,反而会使竹笋的鲜美更加突出。烹饪时,待肉熟后应将肥肉去除,汤汁也不宜多留,只需保留其精华,再加入清汤调和。调味时,只需醋与酒即可。这便是烹饪荤笋的大致方法。竹笋不仅单独食用或搭配其他食材都能展现其美味,更妙的是它还能作为调和之物,提升各种食材的风味。正如菜肴中的竹笋与药物中的甘草一样,都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。有了竹笋的加入,各种食材都能变得更加鲜美。但使用时应注意,不要使用竹笋的渣滓,而要充分利用其精华。善于烹饪的厨师,都会将焯竹笋的汤水留下,每次做菜时都加入一些,使得菜肴更加鲜美,而食客往往只知食物本身之鲜,却不知这鲜美之源乃是竹笋之汤。《本草》中所记载的许多食物,有的虽然对人体有益却不一定可口,有的虽然可口却不一定有益健康。而竹笋则能两者兼顾,既美味又健康。苏东坡曾说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其实,竹笋不仅能治愈人的俗气,还能让人保持健康,避免瘦弱。只不过,这里的“竹”有已成之竹与未成之笋之分罢了。
注释
躯骸:躯壳;身体。
口腹:口和腹,多指饮食。吃喝。
爱育:爱护养育。
蜩螗:蝉的别名。
溪壑:溪谷。
芳馥:芳香。
松脆:谓食物酥脆味美。
豕:猪。
庖人:厨师。>